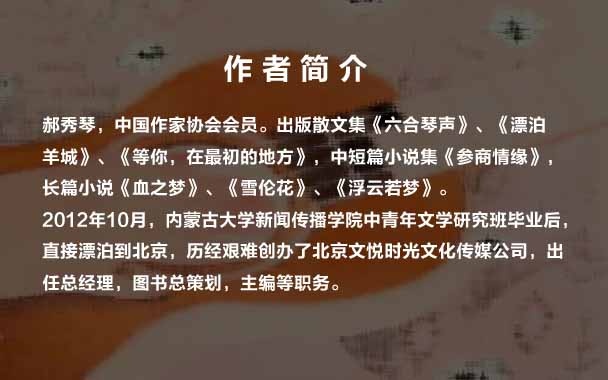那泪,湿了我这辈子的心
2017-04-03 | 点击量: | 作者:郝秀琴
父亲走了,我怎么也不相信,他怎么说走就走了呢?一撒手,让我这辈子再也看不见他的身影。我再也不能做他的女儿了。
昨夜,梦见了父亲,这是他第一次给我托梦。他还是穿着早年那身蓝哔叽中山服,戴一顶蓝色的直贡呢帽子,站在门外久久地望着我,父亲,您怎么来了?我起身开门迎候,父亲却一句话也没有说,将脸转向黑暗。
“爹……”我大声哭喊着,从梦中惊醒……
父亲走了已经整整两年,但他的身影总是在我眼前挥之不去。我总是看见他每天双腿蹒跚着,一步一步向大门外走去,他睁着一双花昏的眼,眺望门前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,期盼着儿女们再回家团聚。夏日,他依旧坐在院子里,看着那盆盛开的海娜花,点燃一支烟慢慢抽着……冬天下雪的时候,他依旧早早起来,用那双苍老的双手握着扫帚,弓着的腰弯着背,轻轻地扫着院里的白雪……
在我的记忆中,小时候父亲就不大喜欢我,我和他是同一天生日,同一个属相。听老年人说,一个家里如果出现这种奇妙的巧合,那是难得的喜事,预示这家的日子会越过越兴旺。可惜我是个女孩,要是个男孩,将来定会光宗耀祖。妈也惋惜地说:“你要是个男孩就好了,长大了能给顶门立户。”父亲常说我是他的克星,这个和他相克一生的女儿,骨子里天生就有一些叛逆的东西,很小的时候,就想离开这个家,想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。15岁那年,我怀着一个美丽的梦,选择了上山下乡。
一个小木箱,一捆行李,就是我下乡的所有东西。母亲一直送我走进站台,我不敢看妈妈那种难舍难离的眼神,车子眼看就要开了,我突然看见站台上奔跑的父亲,他不住地挥动双手,终于上气不接下气跑到车窗下,从贴身口袋里掏出两块钱递给我:“拿着,想家了就回来。”“爹!”我哇地一声哭了。喇叭里播放着:“送亲友的同志赶快下车了……”此刻,我看到泪珠在父亲的眼里打转,心顿时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,一阵疼痛。我第一次觉得,原来父亲是爱我的。我不由地对着车窗大哭起来。
“她是从针眼儿里逃出条命。”母亲哭得泣不成声。
“爹对不起你……”
“我不怨你,真的不怨!是我前世欠人家的血债。”父亲的泪泡软了我的心。
“油毡是公家的,能随便拿吗?”父亲是建筑公司老实本份的红管家。工地所有的建筑材料都由他保管,油漆、玻璃、灯泡、电线、各种家用产品应有尽有。但领料单上如果没有工长的签字,就是亲爹热娘也别想从他手里拿走一斤油漆一块玻璃。
“破油毡到你手里也值钱了。我去垃圾堆上捡几块总不犯法吧!”妈的话把我爹呛得不吭声了。
盖房子的方案初步定了下来。一开工,最辛苦、劳累的是我三个弟弟,每天下班后,匆匆吃罢饭,就开始紧张地干活,大弟扛着铁锹镢头,二弟和三弟推着一辆小铁车,去西山拉运石头。妈和妹妹负责从后厂里捡碎砖块。父亲每天下班回来时,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后座上不是拖着破油毡就是碎条玻璃。砖、瓦、椽檩堆在院子里。那是一个星期日,我们全家出动,父亲还专门请来他们单位一个瓦匠来帮工,挑水和泥的,搬运石头的,垒墙递砖的。从早晨忙到傍晚。小房子终于盖起来了。这间小茅屋,从外面看有点支离破碎,但在我眼里却非常完美。不足三尺宽的窗户上,一块块玻璃都是用二寸宽的玻璃条拼对起来的。阴雨连绵的秋天,雨点击打着屋顶上的油毡,在这声音的伴奏下,我会目不转睛地望着如注的雨水顺着屋檐流下来,一块块红蓝混杂的砖头被洗剥得干干净净,红得更红,蓝得更蓝。父亲母亲给予我那份无以用语言描述的慈爱,深深铭刻在心里。他们尽管不识字,但总是希望自己的女儿将来能干一点大事,成为一个文化人,父亲一生目不识丁。文化大革命的时候,他受了不少冤枉气,那时候,无论干什么事,首先让你背诵毛主席语录。到商店里那怕买一盒火柴,也得先背语录。父亲记不住那些生涩的内容,于是,红卫兵就拦住不让走。后来,我教给他两句最简单的语录:“下定决心,不怕牺牲。”他记住了,并且把这两句话变成教训我们的口头禅。每逢听到别人夸他的女儿会写文章时,总是淡淡一笑:“这孩子灵性像她妈。”每天下班后,父亲总要先推开小屋的门,给我送一壶水。冬天,总是早早地把那个小铁炉点着,把火捅得旺旺的。在我的记忆中。那段日子最温馨安谧,让我这颗破碎的心得到了静养。
望一树红棉开了又谢,大雁南归又北去,我面对波澜不惊的珠江水,思念之情紧紧撕咬着我的心。父亲,我何尝不想回去?有一天,与香港一位易经大师闲聊,无意中谈起我的父亲,谈起我对家的思念,还有自己不能尽孝心的自责和亏欠,大师看着我满眼含泪的样子,就让我在纸上随便写几个字,并问了我的生辰八字。我写了“想家”两个字, 随后他说,你还是在南方好,木命之人,必须到有水之处,身无居所、走南闯北是你命定的,你父亲给了你生命,但你原本和他不是在一个气场,你今生只是他的女儿,虽然有父女的血缘,但命格不一,相互必然排斥,你远离他也好,他会更健康。大师的话让我的心平静了许多,突然想起龙应台的话:“所谓父女母子一场,只不过意味着,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。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,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,而且,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:不必追。”
海娜花开了,母亲在电话里说:“回来吧,明年你父亲还不知道能不能再看到海娜花开。”那时候,我正在内蒙古大学读书,呼和浩特距离集宁很近,坐两个小时的火车就到家了。父亲已经走不了路了,弟弟给买了拐杖、大小便用的座椅。他连家门也出不去了,每天从炕沿边挪动到地桌边,继续喝那杯小酒,这是父亲坚持几十年的习惯,下酒菜也很简单,花生米、咸菜、酱豆腐,他一辈子粗茶淡饭,身体没有什么大毛病,只是浑身瘙痒,全身抓得没有一块好肉皮。他见到我,最多问一句:“你回来了?”我点点头,然后就烧满满一锅开水,把海娜花泡在水里,我带着胶皮手套,用毛巾给父亲热敷全身,父亲的前胸、后背、胳膊、双腿都是血淋淋的,有的肉皮刚刚结了痂又被抓破。我给父亲热敷了全身,抹了药膏,然后就给他洗脚。我说:“海娜花能治疮疖肿疼、能解毒。”父亲说:“那明年多种一些。”给父亲换了洗干净的被褥,他微闭双眼舒服地躺着,一会儿又安顿我母亲:“说你,把那些海娜花籽放好,明年开春多种几盆,你大姑娘爱染指甲。” 听了这活,我转过脸扑簌簌地掉眼泪。我小的时候,母亲种海娜,只是等花开时给她的女儿染指甲。如今,父亲年年种海娜,是等花开时看见她的大女儿回家。
父亲的神志始终是清楚的,当我坐在他身边,握住他那双青筋爆满的双手时,我看见一行老泪从他的眼角流出。
“爹!我回来了。”
“回来就好,爹不能再给你种海娜花了……花籽你妈保存着……”
父亲,你不会走的。我紧紧拉住他的手,生怕他松开。父亲已经不能下床了,他只是想吃冰凉的雪糕,弟弟请来了大夫,诊断后说:“安顿后事吧,心肝五脏都已经衰竭。”
之后的二十天,我和弟弟妹妹一直守在父亲身边。他再不能进食,但一直不停地排泄,我们给他身下铺了尿不湿,不停地给擦洗,抬着他那骨瘦嶙峋的身体翻来翻去,生怕长了褥疮。
接下来的日子,父亲基本处于昏迷状态,偶然清醒了,只是说想吃雪糕,想喝冰水。我继续给父亲热敷全身,给他洗脚洗脸。半夜,不时把手放在父亲的鼻孔下,生怕他呼吸一下停止,我们明明知道父亲在这个世上弥留时间的越来越短了,但心里却无法接受他离去的这个现实,害怕那一刻的到来。弟弟给父亲理了头发刮了胡须,洗了脚,剪了手指甲、脚趾甲。有一天,父亲突然好了许多,他竟然坐起来让我给穿衣服,我给父亲穿好衣服,扶他坐起来,他还说要下地走走,我们都高兴地笑了,以为父亲病情好转,只有母亲心里清楚,她说:“你父亲回光返照了。怕是熬不过今夜。”
那天,我们七个孩子都围在父亲身边。安静地守候着。父亲一句话也不说,默默地望着我们。
那夜,一张白麻纸盖住了他的脸 ……
入殓的时候,我想掀起那张纸再看看父亲,阴阳先生说不要看了 ,阴阳两界一纸之隔,看一次给他加一次罪。不!哪怕只看一眼。我不顾众人的阻拦,还是掀起了那张纸。“爹……”我伏在父亲冰凉的身上泪水整个心。父亲啊,你怎么就这样一撒手走了呢?今生父女一场难道是缘分已尽?
父亲是太阳,母亲是月亮。太阳突然衰落了,我的心顿时变得暗淡无光,因为失去的永远不会再回来,太阳只有一个,什么也无法来弥补和代替他曾经给过你的温暖和光明。我的心再无处取暖。
父亲是土葬的。钉棺的时候,我再次看了他的遗容,弟弟用棉球蘸着酒给父亲一点一点洗着眼睛、两鬓、胡须,他的动作十分缓慢,生怕惊醒了熟睡的父亲。我再次凝望那张慈善的面孔,好想拉起他那冰凉的双手说一声;“父亲,下辈子我还做你的女儿,我会好好孝顺你,不会再让你为我流泪……”这是我和父亲见的最后一面。阴阳先生说;“这老人善眉善眼的,
看得出是个善良之人。如果开光的时候,面孔变了,灵魂必定下了地狱,有的变成驴头马面,非常可怕。”父亲,你的灵魂究竟到了哪里?我虽然不知道,但我知道你走得很安详。安息吧!女儿永远思念你。
父亲出殡前,扫墓之时,突然大雪纷飞,五月飞雪,很少遇到,开车向逸安陵园走去的时候,弟弟感慨地説:“雪盖墓,出殡难遇的好兆头!”
怎么选择了这样一个雪天,我的悲伤被大雪渲染,父亲!我好想知道,你那里也下雪吗?父亲!下辈子我们还是父女吗?
昨夜,梦见了父亲,这是他第一次给我托梦。他还是穿着早年那身蓝哔叽中山服,戴一顶蓝色的直贡呢帽子,站在门外久久地望着我,父亲,您怎么来了?我起身开门迎候,父亲却一句话也没有说,将脸转向黑暗。
“爹……”我大声哭喊着,从梦中惊醒……
父亲走了已经整整两年,但他的身影总是在我眼前挥之不去。我总是看见他每天双腿蹒跚着,一步一步向大门外走去,他睁着一双花昏的眼,眺望门前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,期盼着儿女们再回家团聚。夏日,他依旧坐在院子里,看着那盆盛开的海娜花,点燃一支烟慢慢抽着……冬天下雪的时候,他依旧早早起来,用那双苍老的双手握着扫帚,弓着的腰弯着背,轻轻地扫着院里的白雪……
在我的记忆中,小时候父亲就不大喜欢我,我和他是同一天生日,同一个属相。听老年人说,一个家里如果出现这种奇妙的巧合,那是难得的喜事,预示这家的日子会越过越兴旺。可惜我是个女孩,要是个男孩,将来定会光宗耀祖。妈也惋惜地说:“你要是个男孩就好了,长大了能给顶门立户。”父亲常说我是他的克星,这个和他相克一生的女儿,骨子里天生就有一些叛逆的东西,很小的时候,就想离开这个家,想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。15岁那年,我怀着一个美丽的梦,选择了上山下乡。
一
下乡插队的时候我带了一个破旧的小木箱,行李也很单薄,那年代,棉花和布都按人头供应,一个成人一年供应六尺布票,一斤棉花,高个子人还不够缝一条裤子呢。褥子很薄,母亲想给再添续一些棉花,但没有棉花小票。父亲说,女孩子千万不能睡凉炕,拿块毡子吧,母亲说,一块毡子好贵啊,哪能买得起。父亲不由分说,把炕上铺的那块黑毡子,用剪刀剪下二尺宽的一条。“咱们在家里每天睡火炕,铺不铺毡子都行。还有,把我那件皮袄也拿上。”我执意不要,父亲生气了,沉下脸说:“傻姑娘,这般时候了你还耍洋气看好看,穿上不冷就行了。”父亲的话说得我心里一阵酸楚:“您上班穿啥?”每天从大桥西往大桥东跑,没有皮袄怎能顶住那刺骨严寒。父亲不以为然地笑笑说:“给你穿了,我心暖。”一个小木箱,一捆行李,就是我下乡的所有东西。母亲一直送我走进站台,我不敢看妈妈那种难舍难离的眼神,车子眼看就要开了,我突然看见站台上奔跑的父亲,他不住地挥动双手,终于上气不接下气跑到车窗下,从贴身口袋里掏出两块钱递给我:“拿着,想家了就回来。”“爹!”我哇地一声哭了。喇叭里播放着:“送亲友的同志赶快下车了……”此刻,我看到泪珠在父亲的眼里打转,心顿时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,一阵疼痛。我第一次觉得,原来父亲是爱我的。我不由地对着车窗大哭起来。
他一再吩咐:”想家了就回来,家里不缺你那口吃。”车子缓缓前行,父亲一边抹眼泪,一边跟着火车在站台上疾步追赶……
二
从手术台下来,已是黄昏。橘红色的晚霞映在玻璃窗上,病室里少有的安静。所有的阳光都向我涌来。活过来了。活着就是好,能继续看到阳光,呼吸到空气,看到守在我身边的亲人。门开了,走进来的是父亲,他满眼含泪走到我床前,喊着我的乳名:“娥子……娥子……”我无法说话,此刻,即使说一个字也困难,连眨一下眼睛的气力都没有了。每一个轻微的动作都会使引来剧烈的疼痛。父亲掏出几张十元票子,压在我的枕下。我想摇摇头,但缠着绷带的头却不能自如转动。我想说:“父亲,我好着哩……我只是去阎王殿走了一圈,阎罗正好打盹睡觉,没有从生死册上划掉我的名字。我不是又回来了吗?”嘴唇蠕动着但发不出声音。“她是从针眼儿里逃出条命。”母亲哭得泣不成声。
“爹对不起你……”
“我不怨你,真的不怨!是我前世欠人家的血债。”父亲的泪泡软了我的心。
“出医院后回家吧。”这句话再次证明父亲是爱我的。他容许了我这个嫁出的女儿再次回家居住。此刻我记不起他对我所发的脾气,也记不起对我的冷漠。
三
经历了一场生死搏斗的我,终于从婚姻的枷锁中挣脱出来。在娘家居住的那段日子,父亲为我操心最多。那时,弟弟妹妹都没成家立业,本来就十分拥挤的屋里又加了我和女儿,全家八口人挤在不足六十平米的屋里,别说想安静的看书写作,就连吃饭、睡眠也无法进入正常状态。“给你姐盖一间小房子吧,她爱看书爱清静。”妈的话刚落音,全家人都傻眼啦。父亲第一个表示反对:“砖没一块,檩没一根,拿什么去盖房?”是呀,什么也没有,怎么盖房子?母亲却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,不紧不慢地说:“厂子里不是处理半头砖,一块钱一小车,拉上十几车还不够盖间房?土、沙子、石头西山上有的是,用不着花钱买,咱们辛苦点自己往回拉运不就行啦,至于房顶咱也不盖瓦,让你爹拿几块破油毡回来。”“油毡是公家的,能随便拿吗?”父亲是建筑公司老实本份的红管家。工地所有的建筑材料都由他保管,油漆、玻璃、灯泡、电线、各种家用产品应有尽有。但领料单上如果没有工长的签字,就是亲爹热娘也别想从他手里拿走一斤油漆一块玻璃。
“破油毡到你手里也值钱了。我去垃圾堆上捡几块总不犯法吧!”妈的话把我爹呛得不吭声了。
盖房子的方案初步定了下来。一开工,最辛苦、劳累的是我三个弟弟,每天下班后,匆匆吃罢饭,就开始紧张地干活,大弟扛着铁锹镢头,二弟和三弟推着一辆小铁车,去西山拉运石头。妈和妹妹负责从后厂里捡碎砖块。父亲每天下班回来时,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后座上不是拖着破油毡就是碎条玻璃。砖、瓦、椽檩堆在院子里。那是一个星期日,我们全家出动,父亲还专门请来他们单位一个瓦匠来帮工,挑水和泥的,搬运石头的,垒墙递砖的。从早晨忙到傍晚。小房子终于盖起来了。这间小茅屋,从外面看有点支离破碎,但在我眼里却非常完美。不足三尺宽的窗户上,一块块玻璃都是用二寸宽的玻璃条拼对起来的。阴雨连绵的秋天,雨点击打着屋顶上的油毡,在这声音的伴奏下,我会目不转睛地望着如注的雨水顺着屋檐流下来,一块块红蓝混杂的砖头被洗剥得干干净净,红得更红,蓝得更蓝。父亲母亲给予我那份无以用语言描述的慈爱,深深铭刻在心里。他们尽管不识字,但总是希望自己的女儿将来能干一点大事,成为一个文化人,父亲一生目不识丁。文化大革命的时候,他受了不少冤枉气,那时候,无论干什么事,首先让你背诵毛主席语录。到商店里那怕买一盒火柴,也得先背语录。父亲记不住那些生涩的内容,于是,红卫兵就拦住不让走。后来,我教给他两句最简单的语录:“下定决心,不怕牺牲。”他记住了,并且把这两句话变成教训我们的口头禅。每逢听到别人夸他的女儿会写文章时,总是淡淡一笑:“这孩子灵性像她妈。”每天下班后,父亲总要先推开小屋的门,给我送一壶水。冬天,总是早早地把那个小铁炉点着,把火捅得旺旺的。在我的记忆中。那段日子最温馨安谧,让我这颗破碎的心得到了静养。
四
决定去广州的时候,父亲没有挽留我,他太了解自己的女儿了。但在我离开家的那一刻,却看见他老泪横流,他蠕动着嘴唇想说什么,但一个字也没有说出来。我好想上前抓住他的手,说一声:“父亲,我会回来看你的……”但万万没想到,这一走就是五年。记得那年他八十岁生日时,在电话里只说了一句话:“只盼有生之年再见你一面。”听到他的声音我放声痛哭,思念之情如潮水汹涌,父亲不知还能不能等到我回去?父女俩还能在一起过一个生日吗?小时候和父亲一起过生日的情景历历在目,想起他给我买的那个不倒翁,那是父亲第一次送我的生日礼物,这个不倒翁一直伴我度过童年。此刻,我才感觉到自己是多么思念父亲,我好想再听到他那常常斥责我的生硬的喊叫声,听听他每当夜里那如雷的呼噜声……望一树红棉开了又谢,大雁南归又北去,我面对波澜不惊的珠江水,思念之情紧紧撕咬着我的心。父亲,我何尝不想回去?有一天,与香港一位易经大师闲聊,无意中谈起我的父亲,谈起我对家的思念,还有自己不能尽孝心的自责和亏欠,大师看着我满眼含泪的样子,就让我在纸上随便写几个字,并问了我的生辰八字。我写了“想家”两个字, 随后他说,你还是在南方好,木命之人,必须到有水之处,身无居所、走南闯北是你命定的,你父亲给了你生命,但你原本和他不是在一个气场,你今生只是他的女儿,虽然有父女的血缘,但命格不一,相互必然排斥,你远离他也好,他会更健康。大师的话让我的心平静了许多,突然想起龙应台的话:“所谓父女母子一场,只不过意味着,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。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,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,而且,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:不必追。”
五
当再见到父亲的时候。他苍老了许多。五年啊,岁月毫不留情地压弯了他的脊骨和双腿,他再也不能走到大门外闲坐了,天气暖和的时候,就搬着马扎,坐在自家门口,院里有几盆花,都是父亲春天种下的,最早盛开的是五月梅,接着就是海娜花,最后是那盆金菊,花谢了的时候,父亲总是把花籽从枯朽的枝叶间抖落下来,一粒一粒用烟盒纸包起来,并高声喊母亲:“说你,给我把花籽放好了,开春了再种。”父亲一辈子没有叫过母亲的名字,“说你”是父亲称呼母亲的专用名称。他哆嗦着手把纸包递给母亲。母亲问:“海娜花籽捡了没有?”父亲没好气地说:“我能不捡?你就怕我少种了海娜花。”“你大姑娘喜欢这花,小时候,她就是盼海娜花开,花一开她就缠着我给她染指甲。”母亲总想絮絮叨叨讲着我小时候的故事。“明年多种几盆,你没听电视里说,海娜花还能染头发,花开了你打电话叫她回来。”这些话都说母亲告诉我的。我知道父亲一直看不惯我的言行举止,看不惯我的衣着打扮,每次回家,我绝对不敢穿着大红裤子面见父亲,母亲告诉我父亲每年种海娜花,只是为了那个从小喜欢染红指甲的女儿,听了母亲的话,我心里总是沉甸甸的难过,我知道父亲还是爱我的,他心里原来一直放心不下我。我也期待着院里那片海娜花盛开的时候,我希望将那美丽的花朵放到父亲温热的掌心。小时候,妈妈没有钱给我买指甲油。就在院里种了一片海娜花,每逢海娜花开了的时候,妈妈就捡拾落地的花儿,洗干净放在碗里,用擀面杖捣碎了,里面放一点点石灰,然后,就把那花浆涂在我指甲上,再用布将我的十个指头包起来,整整包裹一夜,第二天,我的指甲被染成了橘红色。所以,我对海娜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。海娜花开了,母亲在电话里说:“回来吧,明年你父亲还不知道能不能再看到海娜花开。”那时候,我正在内蒙古大学读书,呼和浩特距离集宁很近,坐两个小时的火车就到家了。父亲已经走不了路了,弟弟给买了拐杖、大小便用的座椅。他连家门也出不去了,每天从炕沿边挪动到地桌边,继续喝那杯小酒,这是父亲坚持几十年的习惯,下酒菜也很简单,花生米、咸菜、酱豆腐,他一辈子粗茶淡饭,身体没有什么大毛病,只是浑身瘙痒,全身抓得没有一块好肉皮。他见到我,最多问一句:“你回来了?”我点点头,然后就烧满满一锅开水,把海娜花泡在水里,我带着胶皮手套,用毛巾给父亲热敷全身,父亲的前胸、后背、胳膊、双腿都是血淋淋的,有的肉皮刚刚结了痂又被抓破。我给父亲热敷了全身,抹了药膏,然后就给他洗脚。我说:“海娜花能治疮疖肿疼、能解毒。”父亲说:“那明年多种一些。”给父亲换了洗干净的被褥,他微闭双眼舒服地躺着,一会儿又安顿我母亲:“说你,把那些海娜花籽放好,明年开春多种几盆,你大姑娘爱染指甲。” 听了这活,我转过脸扑簌簌地掉眼泪。我小的时候,母亲种海娜,只是等花开时给她的女儿染指甲。如今,父亲年年种海娜,是等花开时看见她的大女儿回家。
六
春天,父亲病倒了,接到妹妹打来的电话,我扔下了所有的工作,不顾一切往家里赶。坐在火车上,我一路祈祷一路流泪,父亲一生的点点滴滴在我的大脑里回放,他秉性耿直,是个不会说半句谎话的老实人,他对我们的言传身教也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。他不容许儿女们做出一点点违规的事,做人光明磊落,办事堂堂正正是父亲留给我们的唯一家训。父亲的神志始终是清楚的,当我坐在他身边,握住他那双青筋爆满的双手时,我看见一行老泪从他的眼角流出。
“爹!我回来了。”
“回来就好,爹不能再给你种海娜花了……花籽你妈保存着……”
父亲,你不会走的。我紧紧拉住他的手,生怕他松开。父亲已经不能下床了,他只是想吃冰凉的雪糕,弟弟请来了大夫,诊断后说:“安顿后事吧,心肝五脏都已经衰竭。”
之后的二十天,我和弟弟妹妹一直守在父亲身边。他再不能进食,但一直不停地排泄,我们给他身下铺了尿不湿,不停地给擦洗,抬着他那骨瘦嶙峋的身体翻来翻去,生怕长了褥疮。
接下来的日子,父亲基本处于昏迷状态,偶然清醒了,只是说想吃雪糕,想喝冰水。我继续给父亲热敷全身,给他洗脚洗脸。半夜,不时把手放在父亲的鼻孔下,生怕他呼吸一下停止,我们明明知道父亲在这个世上弥留时间的越来越短了,但心里却无法接受他离去的这个现实,害怕那一刻的到来。弟弟给父亲理了头发刮了胡须,洗了脚,剪了手指甲、脚趾甲。有一天,父亲突然好了许多,他竟然坐起来让我给穿衣服,我给父亲穿好衣服,扶他坐起来,他还说要下地走走,我们都高兴地笑了,以为父亲病情好转,只有母亲心里清楚,她说:“你父亲回光返照了。怕是熬不过今夜。”
那天,我们七个孩子都围在父亲身边。安静地守候着。父亲一句话也不说,默默地望着我们。
那夜,一张白麻纸盖住了他的脸 ……
入殓的时候,我想掀起那张纸再看看父亲,阴阳先生说不要看了 ,阴阳两界一纸之隔,看一次给他加一次罪。不!哪怕只看一眼。我不顾众人的阻拦,还是掀起了那张纸。“爹……”我伏在父亲冰凉的身上泪水整个心。父亲啊,你怎么就这样一撒手走了呢?今生父女一场难道是缘分已尽?
父亲是太阳,母亲是月亮。太阳突然衰落了,我的心顿时变得暗淡无光,因为失去的永远不会再回来,太阳只有一个,什么也无法来弥补和代替他曾经给过你的温暖和光明。我的心再无处取暖。
父亲是土葬的。钉棺的时候,我再次看了他的遗容,弟弟用棉球蘸着酒给父亲一点一点洗着眼睛、两鬓、胡须,他的动作十分缓慢,生怕惊醒了熟睡的父亲。我再次凝望那张慈善的面孔,好想拉起他那冰凉的双手说一声;“父亲,下辈子我还做你的女儿,我会好好孝顺你,不会再让你为我流泪……”这是我和父亲见的最后一面。阴阳先生说;“这老人善眉善眼的,
看得出是个善良之人。如果开光的时候,面孔变了,灵魂必定下了地狱,有的变成驴头马面,非常可怕。”父亲,你的灵魂究竟到了哪里?我虽然不知道,但我知道你走得很安详。安息吧!女儿永远思念你。
父亲出殡前,扫墓之时,突然大雪纷飞,五月飞雪,很少遇到,开车向逸安陵园走去的时候,弟弟感慨地説:“雪盖墓,出殡难遇的好兆头!”
怎么选择了这样一个雪天,我的悲伤被大雪渲染,父亲!我好想知道,你那里也下雪吗?父亲!下辈子我们还是父女吗?
“父女情深留不住鹤归去,骨肉缘深只化作泪如雨。”滂沱泪雨,湿了坟头的绿草,湿了那棵幡树,也湿了我这辈子的心!